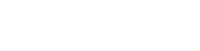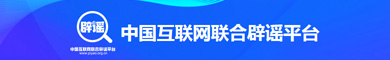百歲老人鄭逸梅生活管窺
多年前購得“補(bǔ)白大王”鄭逸梅先生的《藝林散葉》,很厚的一部,六百多頁,收了老先生所寫的藝界聞人軼事六千多則。每則長則一二千字,短則一二百字。很適合隨時(shí)拿上手,隨意翻到一頁,然后慢慢咀嚼,就似欣賞一幕幕的短劇,很有味道。
平時(shí)有些空閑,拿來翻開,無需挑揀,就這么慢慢讀下去,開眼界,長見識(shí),頗為雅事一件。這本書的最后一輯,是鄭老寫自己一些感悟及生活情趣之類,二百多則,就十八頁。細(xì)細(xì)讀來,老人的生活、情感、見識(shí),都有展露。
無怪乎鄭老高壽至98歲,無怪乎鄭老一生筆耕不輟,從不懈怠,無怪乎老人的思路直到晚年依然清晰。盡管二百多則筆記中尋覓到他的生活點(diǎn)滴比較零碎,不完整,但從中可以捕捉到老人的作息習(xí)慣,對(duì)如今類似我等已入老境的人來說,是很有啟發(fā)的。
讀完這二百多則筆記,能感覺到鄭老長壽健康的原因有幾點(diǎn):生活不講究,衣食隨意,沒有陋習(xí),心態(tài)平和。如他寫自己的生活習(xí)慣:一輩子睡硬板床。他說:“余睡板床數(shù)十年,體力仍健好也。”“余臥木板床數(shù)十年,從未有沙發(fā)床、彈簧床之享受,卻老而彌健。近據(jù)醫(yī)學(xué)界人士談,從人體生理衛(wèi)生角度出發(fā),最好之睡床,乃木板床,則余固先知先覺之實(shí)行家。”
這習(xí)慣,本人倒是與老先生有同感。小時(shí)候在上海睡棕繃,還比較硬扎。下放到安徽農(nóng)村,床框子上用苘麻繩橫豎攔幾十道,就不習(xí)慣,人像蕩在中間。招工進(jìn)城,患上腰椎間盤突出,治療后醫(yī)生關(guān)照睡硬板床。其時(shí)剛調(diào)到新單位,職工有福利,公家送床一張。我從上海買了床架運(yùn)來,告訴單位,床架有了,給我打個(gè)鋪板即可。尺寸量好,做一木框,里面用木板鋪實(shí),躺著很舒服。木頭不像棕繃會(huì)壞,不像苘繩會(huì)松,很穩(wěn)當(dāng)。
一睡就睡到了六十歲退休回上海,此間腰病再無復(fù)發(fā)。其間如出差睡賓館,太軟的彈簧床就覺得難受,第二天渾身酸痛。到上海之后,原來買的床墊也是彈簧床,睡幾年后,覺得還是板床舒服,于是去買了一張鋪板,鋪在彈簧床上面(彈簧床抽掉床太矮)。看來硬板床是要睡到底了。
說到心態(tài)好,那是人保持健康的根本。鄭老記下這樣一則:“我喜撰小品文,散刊各報(bào)。關(guān)外某報(bào)轉(zhuǎn)載之,截去署名。某抄襲家不知也,乃抄錄一過,投寄《金剛鉆報(bào)》。時(shí)我適主該報(bào)筆政,閱之嗢噱。”最后“嗢噱”一詞第一次見,查了下,乃是:笑不止,樂不自勝。
副刊編輯往往會(huì)碰到這樣的事。當(dāng)年蘇北某地農(nóng)村有一投稿人,每每一次性寄來十來篇散文稿,是在那種鄉(xiāng)鎮(zhèn)小印刷作坊里印出來像傳單一樣的。其實(shí)就是抄來的,廣種薄收,向全國幾百家報(bào)紙投稿。萬一有幾篇刊出,也有一筆收入。對(duì)這種來稿,立馬扔字紙簍,且極反感。
我們當(dāng)?shù)赜型陡逭撸€是個(gè)執(zhí)法部門的工作人員,第一次抄了一篇散文寄來,我覺得不錯(cuò),就發(fā)了。他嘗到甜頭,再接再厲,又抄一篇發(fā)過來。這次他膽子大了,把余秋雨的散文抄來了。覺得眼熟,一查,原來如此。再查他前一篇,是抄蕪湖的一位作者的。于是惱火得很,前一篇的稿酬追回,又通報(bào)其他科室,注意此人。
還有位作者,寫得也不錯(cuò),偏偏去抄《散文》雜志上的文字,被其他編輯看出來了。本來我是欣賞他的,這一來就像碰到了騙子,從此封殺他的稿件。那一段時(shí)間也是郁悶得很。像鄭老那樣大度,一笑了之,我恐怕還做不到,肯定是耿耿于懷。
鄭老筆耕終生,當(dāng)然也有他的業(yè)余生活,從書中可以看到,老先生的喜好,有交友,有讀書,有收藏,也有賞花。老先生交往人多,朋友自然不少。他叫兒子替他編一個(gè)通訊錄,以姓氏筆畫多少排序。結(jié)果編出了一“巨冊(cè)”。像我們過去沒有使用手機(jī)前的通訊錄,不過小小薄薄一本,百多人名地址電話。而這個(gè)巨冊(cè)恐怕得有上千人之多。
書中有文:“我收藏紅豆凡四種:一為吳中天池山物,荊人周壽梅自岳家?guī)恚欢榻庮櫳郊t豆樹下物,乃吳鳳鳴見貽者;而俞友清饋我虞山紅豆山莊所產(chǎn)者二枚,南洋群島者二枚。尤以南洋者,殷然渾圓,如寶石之有光,為之愛不釋手,毋怪王摩詰有‘紅豆生南國’之句也。”
又記:“徐積余藏戊戌六君子手札,逝世后散出。我購得譚嗣同二札一名片,浩劫中散失。”又記:“有人以呂留良賣地券出讓,索價(jià)五十金,我欲購,卻被人先得,至今惜之。”又記:“我得傅青主畫幅,楊宛叟見而羨之,我以宛叟為長者,不與爭,畫卒歸宛叟。”這種收藏,純粹文人所好,欣賞把玩,不圖回報(bào)。碰到對(duì)眼的收入,被人捷足先登也無所謂。
而讀書顯然是老先生生活中又一要?jiǎng)?wù)。且看:“恨不得十年暇,讀平生未見之書,涉從未至之境。”又記:“不讀書,不看云,不焚香,不寫字,則雅趣自消,俗塵自長。”又記:“天下惟善讀書者,不負(fù)花月,不脫酒盞,不離山水,不絕美人。”又記:“冬夏讀書,春秋游覽,此是世間惟一福人。”這樣的讀書,誰又能說不是種享受。
所以,在這十八頁文字中,鄭老說出了自己一生的夢(mèng)想:“若得地十畝,必以三畝植梅,三畝樹竹石,一畝鑿蓮沼,而所余三畝,則筑屋庋藏文史圖譜,鼎硯骨董,予偃仰舒嘯其中,以度晨夕,此外則無所求矣。”這是一個(gè)文人的夢(mèng),美好,樸素,簡約,可以說這是上千年來所有純文人的夢(mèng)想。
在蘇州揚(yáng)州那樣的地方,我們現(xiàn)今可以看到這些夢(mèng)的影子。一個(gè)在文壇上活躍了近一個(gè)世紀(jì)的老人有這樣的夢(mèng),非常自然。盡管無法實(shí)現(xiàn),但,向往總是可以的。鄭老已故去三十三年了。一個(gè)世紀(jì)老人。從那些短短的文字中,看到他生活中曾經(jīng)的點(diǎn)滴,感到他思維中躍動(dòng)的亮點(diǎn),仿佛老人依舊在與我們促膝而談。
■ 王仲翔
· 版權(quán)聲明 ·
①拂曉報(bào)社各媒體稿件和圖片,獨(dú)家授權(quán)拂曉新聞網(wǎng)發(fā)布,未經(jīng)本網(wǎng)允許,不得轉(zhuǎn)載使用。獲授權(quán)轉(zhuǎn)載時(shí)務(wù)必注明來源及作者。
②本網(wǎng)轉(zhuǎn)載其他媒體稿件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(wǎng)贊同其觀點(diǎn)和對(duì)其真實(shí)性負(fù)責(zé)。如因轉(zhuǎn)載的作品內(nèi)容涉及您的版權(quán)或其它問題,請(qǐng)盡快與本網(wǎng)聯(lián)系,本網(wǎng)將依照國家相關(guān)法律法規(guī)作相應(yīng)處理。


推薦閱讀
-
1
-
2楊軍接待信訪群眾 06-10
-
3
-
4
-
5
-
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