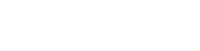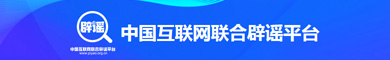燕來燕去
□張炳輝
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來這里。我問燕子你為啥來?燕子說,這里的春天最美麗……”這首童年唱的兒歌,至今難忘。正如有人所說:“留不住的是似水年華,揮不去的是美好記憶。”
20世紀60年代中期,我們家在眾鄉鄰的幫助支持下,蓋起了三間草房堂屋,剛開春搬進新房,沒過多久,就見有對花肚皮的燕子飛進飛出,“啾啾”地叫著,姥姥對我們說:“不要大聲說話,更不要轟它們,它們要到咱們家梁上壘窩孵小燕子呢。這可是咱家的‘喜蟲’,老輩人常說‘燕兒不進苦寒門’呢。”
沒過幾天,就見這對燕子選中堂屋中間的橫樹棍上,從外面一口口銜來濕泥,泥里還混著麥秸,從外圍開始,一層一層把泥團往上摁,然后再銜來干草鋪窩,末了還要叼來軟和的鵝毛墊上,這是它們要準備孵小燕子了。
那時,我剛上小學,暑假在屋里做作業,抬頭瞧見四五只肉團一般鑲著黃嘴圈的小燕,嘴張得像小喇叭,“唧唧唧”地催食,別有一番情趣。最有意思的看老燕子喂食,老燕嘴里叼著蟲子,剛挨近窩邊,小燕們就把腦袋伸得老長,生怕吃不著。對小燕來說,此時家的味道就是食物的味道。有一回,一只小燕太貪心,便從窩里掉下來,好在摔得不重,是父親搬著梯子又把它送到窩里,喜得老燕小燕一起歌唱起來。那時我知道農民手上有繭,那是勤勞人的標志;燕子呢,一口口銜泥壘窩,一口口捉蟲喂小燕,燕子嘴上可能也會有繭,那是它心中有愛。
在城市的小區內、公園里或道路旁,偶爾也能見到翻飛的燕子,盡管這里很少有“苦寒門”,但終歸沒見它們在這鋼筋水泥林立的樓叢間壘窩筑巢、生兒育女,或許他們只是來城里逛逛,開開眼界,并不準備長住。
有人說:“生活并不是一個復雜的問題,而是一連串復雜的問題。”我覺得這話若是用在家鄉燕子的身上倒是很合適。燕子經過艱辛的勞動,終于把小燕育成。入秋時節,小燕羽毛長齊、漆黑透亮,頭回試飛那天,老燕在半空中打轉,“啾啾”地叫著引導它們。有只膽大的先撲棱著翅膀竄出來,在空中打了個旋,又忙不迭地飛回了窩。
該飛來的總會飛來,該飛去的總會飛去。燕子真飛走的那天,我清楚地記得。天剛蒙蒙亮,燕子各奔東西,小燕并未同老燕結伴而行。燕窩里靜悄悄的,往日的熱鬧沒有了,讓人悵然若失。
十年前,我曾寫過一篇同題《記得當年年紀小》的征文,其中寫道:“記得當年年紀小,看著燕子壘窩巢。露出一群小腦袋,嘰嘰喳喳瞎吵鬧。老燕小燕嘴對嘴,呢呢喃喃唱歌謠。娘說,天下父母都一樣,為兒從不說辛勞。老燕盼兒快長大,翅膀硬了又飛了。”近年,家鄉的年輕人,大多像這燕子,長大后就飛向各地,留下老屋檐下的爹娘,守著空蕩蕩的巢,眼巴眼望地等著兒女們歸來。
近日,重讀唐代詩人白居易的《燕詩示劉叟》,當是又一番感慨。詩曰:“梁上有雙燕,翩翩雄與雌。銜泥兩椽間,一巢生四兒。四兒日夜長,索食聲孜孜。青蟲不易捕,黃口無飽期。觜爪雖欲敝,心力不知疲……”
白居易筆下的燕兒,恰似我窗前的常客。春日清晨,總能看見雌雄雙燕如默契的舞者,穿梭在煙雨朦朧間。它們喙間銜著濕潤的泥土,混合著柔軟的草莖,在屋檐下筑起溫暖的巢穴。每一次來回,都是對生命的虔誠勾勒,哪怕風雨打濕羽翼,也未曾停歇。
待雛燕破殼,燕父母便開啟了更加忙碌的日子。它們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天際與巢穴之間,只為滿足雛燕們“索食聲孜孜”的渴望。看著老燕將捕獲的青蟲小心翼翼喂進黃口,那充滿愛意的模樣,讓人動容。而我們一家人,總會默默守護這份生命的成長,不去驚擾。偶爾,雛燕探出腦袋,與我對視,那一刻,仿佛跨越了物種的界限,彼此心意相通。在這屋檐之下,人與自然,動物與人類,共同譜寫著一曲和諧美好的生命樂章。
· 版權聲明 ·
①拂曉報社各媒體稿件和圖片,獨家授權拂曉新聞網發布,未經本網允許,不得轉載使用。獲授權轉載時務必注明來源及作者。
②本網轉載其他媒體稿件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如因轉載的作品內容涉及您的版權或其它問題,請盡快與本網聯系,本網將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作相應處理。


推薦閱讀
-
1
-
2從“質升量穩”看宿州外貿底氣何在? 06-23
-
3宿州傳統“老字號”煥發“新生機” 06-21
-
4楊軍在靈璧縣調研耕地保護、糧食安全等工作 06-20
-
5全市招商引資重點項目暨固定資產投資調度會召開 06-20
-
6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總數達593家 06-20